从《让·桑特伊》到《追忆》,假故事的胜利
【编者按】
《叙事话语》是法国文学理论家、叙事学家热奈特最著名的一部作品,以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为例,为从叙事学角度分析小说文本提供了一套精密的工具。而在《新叙事话语》中,他回答了各国学者对《叙事话语》的批评,对《叙事话语》中的论点作了修正与进一步的阐释,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叙事学上的新问题。本文摘自《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澎湃新闻经新行思授权发布。
在兜过这个新圈子之后,我们将更容易抓住普鲁斯特在《追忆》中有意无意所作的叙述选择的特点。但首先应当指出普鲁斯特在第一部叙述巨作中,更确切地说,在《追忆》的第一个版本即《让·桑特伊》中作了什么选择。在这部作品中,叙述主体是双重的:没有名姓的故事外叙述者(他是主人公的第一个替身,其境遇后来被写成马塞尔的境遇)与一位朋友在孔卡尔诺海湾度假;两个年轻人结识了一位姓C的作家(主人公的第二个替身),他正在写一部小说,应他们的要求,每晚把白天写的段落读给他们听。朗读的这些片段没有记录成文,但几年以后,C去世了,叙述者不知如何拥有了小说的一个抄本,决定拿去发表,这就是《让·桑特伊》,其中的主人公显然就是马塞尔的第三个雏形。这种不连贯的结构也可算作仿古,但与《曼侬·莱斯戈》所代表的传统还有两处细微的差别。故事内叙述者在这里不讲述他本人的故事,他的叙事不是口头的,而是书面的,甚至具有文学性,因为这是一部小说。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第一个差别,它涉及“人称”问题。现在必须着重谈谈第二个差别,它表明在这些手法已经不盛行的时代,作者写小说时畏首畏尾,并且显然需要与比《追忆》更接近自传的让的传记“保持距离”。元故事叙事的文学性和“虚构”性(因为是小说)使叙述的双重性更为突出。
我们应当记住,普鲁斯特在第一阶段并非不知道“抽屉式”的叙述方法,并且曾受到它的诱惑,他在《女逃亡者》中曾影射过这一手法:“小说作者们常常在前言中声称,他们在某国旅行时遇到的某个人向他们讲述了一个人的身世。于是他们便让这个萍水相逢的朋友讲述,他对他们作的叙事恰恰就是他们的小说,如法布里斯·台尔·唐戈的身世便是帕多瓦的一名议事司铎讲给司汤达听的。当我们恋爱的时候,即当我们觉得另一个人的生活十分神秘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找到这样一位知情的叙述者啊!自然,他是存在的。我们自己不是常常毫无激情地把这个或那个女人的身世讲给一位朋友或一位素昧平生的人听吗?他们对这个女人的爱情生活一无所知,好奇地听我们讲述。”看得出来,这段说明不仅关系到文学创作,而且可以推广到最常见的叙述活动,如在马塞尔的生活中可以进行的叙述活动。甲向乙作的有关丙的叙事是编织我们“经验”的经纬线,其中大部分是叙述的经验。
这段往事和这个影射更突出了《追忆》叙述的主要特点,即几乎一贯取消元故事叙事。首先,搜集到手稿这个虚构情节被直接叙述所取代,主人公兼叙述者公开把自己的叙事当作文学作品来介绍,因而与吉尔·布拉斯或鲁滨孙一样,承担起(虚构)作者的角色,与读者大众直接接触。因此,他用“这本书”或“这部作品”来指他的叙事,使用学院式的复数,向读者讲话,甚至写出斯特恩式或狄德罗式的有趣的假对话:“这一切”,读者会说,“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
“这的确令人遗憾,读者先生。而且比你想的还要可悲……”
“阿尔帕荣夫人究竟有没有把你介绍给亲王?”
“没有,你别说话,让我继续讲下去。”
小说《让·桑特伊》的虚构作者没有敢这样写,这个差别可以衡量出叙述者在摆脱束缚方面取得了多大的进展。其次,《追忆》中几乎完全没有元故事的插入,几乎只能举出这些例子:斯万就他与倒向德雷福斯派的盖尔芒特亲王的谈话向马塞尔所作的叙事,埃梅有关阿尔贝蒂娜以往品行的汇报,尤其是被当作龚古尔兄弟手笔的关于维尔迪兰家晚宴的叙事。我们还将注意到,在这三例中,叙述主体被置于引人注目的地位,其重要性与被转述的事情不相上下:斯万幼稚的偏袒比亲王立场的转变更使马塞尔感兴趣;埃梅用书面语体,带着次序颠倒的括号和引号而作的汇报是一篇虚构的仿作,假龚古尔式的叙事,这篇真正的仿作,与其说是关于维尔迪兰沙龙的一份资料,倒不如说是一篇文学作品,一个文学虚荣心的佐证。由于这许多原因,要简化这些元故事叙事,即让叙述者重新承担这些叙事是不可能的。
相反,在《追忆》其他所有的篇章里,常用的叙事方法是我们所谓的假故事,它原则上为第二叙事,但立即被引回到第一层,而且不论来源如何,一律由主人公兼叙述者负责。第一章提到的大部分倒叙或出自主人公的回忆,即某种奈瓦尔式的内心叙事,或出自第三者向主人公作的叙述。比方说,《在少女花影下》的最后几页属第一类,通过主人公回到巴黎后的回忆,追述巴尔贝克阳光灿烂的清晨:“当我回想巴尔贝克时,眼前几乎总浮现出这样的时刻:在气候宜人的季节,每天清晨……”然后,追述忘却了记忆这个托词,以直接叙事自行发展直到最后一页,以致许多读者没有注意到在时空上绕的弯子导致了直接叙事,还以为这不过是没有改变叙述层的同故事的“回顾”;或如用下面这句话引出1916年在巴黎逗留期间对1914年的回顾:“我想我有好久没有再见到这部作品中的任何人了。只是在1914年……”接下去是对这第一次回顾的直接叙事,仿佛这不是在第二次回顾中唤起的回忆,或仿佛这个回忆在这里不过是叙述的借口,即普鲁斯特所说的“过渡手法”;几页之后,描写圣卢来访的一段以同故事的倒叙开始,以“我一面这样回想圣卢的来访……”这句事后揭示记忆来源的话结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贡布雷》的第一部分是失眠时的遐想,《贡布雷》的第二部分是小玛德莱娜蛋糕的滋味激起的“非意愿性回忆”,而自《斯万的爱情》开始,其后的一切章节又都是失眠者的追忆。实际上,整部《追忆》是以“中间主体”的回忆为名,旋即被最后的叙述者当作叙事来要求和承担的长篇假故事倒叙。
上一章谈聚焦问题时提到的全部插曲都属于第二类,这些插曲于主人公不在场时发生,因此叙述者通过中间叙事才掌握了情况,如斯万结婚的前前后后,诺普瓦和法芬埃姆之间的交易,贝戈特之死,斯万死后吉尔贝特的表现,贝尔玛家不成功的招待会。我们看到,这些消息的来源时而公开,时而隐蔽,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马塞尔都把他从戈达尔、诺普瓦、侯爵夫人或天知道什么人那里得来的消息小心翼翼地插入自己的叙事中,仿佛他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他一丝一毫的叙述特权。
《斯万的爱情》是最典型、自然也是最重要的例子。从原则上说,这段插曲是双重的元故事,首先因为该插曲的细节是一个叙述者在某个未确定的时刻转述给马塞尔听的,其次因为马塞尔在某些不眠之夜又回忆起这些细节:这是对以往叙述的回忆,因而在此之后,故事外的叙述者再一次把全部材料捡拾起来,以自己的名义讲述他出生以前发生的这整个故事,并打上自己后来生活的一些难以觉察的印记,这些印记就像是他的签名,使读者不会过久地将他忘却——这是叙述以“我”为中心的精彩一例。普鲁斯特在《让·桑特伊》中尝到了元故事的陈旧的乐趣,一切看上去仿佛他曾发誓再也不用这种手法,把全部叙述职能留给自己(或他的代言人)。由斯万本人讲述《斯万的爱情》恐怕会破坏主体的统一和主人公的垄断。在《追忆》最后的结构中,马塞尔的前替身斯万只应是个不幸的和不完善的先驱,因而他无权“发言”,即叙事,更无权出现于承载和伴随该叙事、并赋予其含义的话语中。因此,最后应当由马塞尔,并且只应当由他撇开其他一切主体来讲述这段他人的艳史。
但是,正如大家所知,这段艳史预示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马塞尔的艳史,这就是上文分析过的某些元故事叙事的间接影响。斯万对奥黛特的爱情原则上对马塞尔的命运没有任何直接影响,为此,古典主义的规范恐怕会认为斯万的爱情纯粹是个插曲;但它的间接影响,即马塞尔通过叙事了解这段爱情后受到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他在《索多玛与蛾摩拉》里亲自作了说明:
于是我想到我所了解的斯万如何爱奥黛特,一生如何受愚弄的全部情况。其实,我所以愿意去想,是因为对别人讲给我听的斯万夫人性格的回忆和我的定见,使我渐渐设想出阿尔贝蒂娜的全部性格,并对我无法完全控制的一个人每时每刻的生活做出痛苦的解释。这些叙事促使我后来设想阿尔贝蒂娜可能不是个好姑娘,可能像老娼妓一样淫荡下流,惯于欺诈,我想象着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爱上她后本该经受的一切痛苦。
“这些叙事促使……”正由于对斯万爱情的叙事,马塞尔有朝一日才确实有可能想象出一个与奥黛特相像的阿尔贝蒂娜(水性杨花,淫荡下流,难以接近)并因此爱上她。后果如何,尽人皆知。叙事的威力何其大焉……
总之,我们不要忘记,俄狄浦斯之所以能够做到每个人据说仅能想想而已的事,那是因为神示事先讲述他有朝一日将杀父娶母:没有神示他不会被放逐,因而不会隐姓埋名,也就不会杀父和乱伦。《俄狄浦斯王》的神示是一个将来时的元故事叙事,一经陈述就会发动足以实现神示的“爆炸装置”。实现的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个以叙事为形式“请君入瓮”的圈套。是啊,叙事多么有威力(又多么诡计多端)!有些叙事让人活下去(山鲁佐德),有些却置人于死地。如果我们不把斯万被人讲述的爱情理解为命运的一个工具,那么我们对《斯万的爱情》就作不出正确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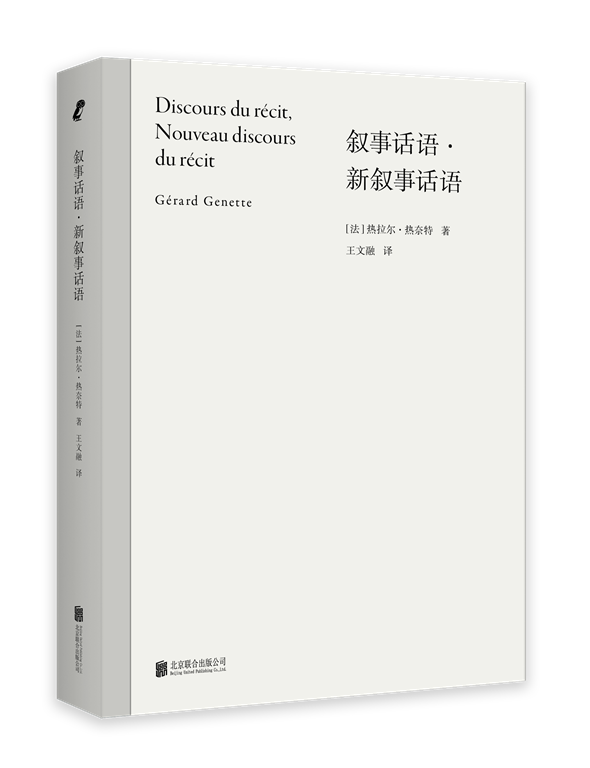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法]热拉尔·热奈特著,王文融译,新行思|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2月。